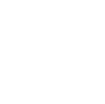我与党的故事
【永远跟党走】 党旗飘扬在万里之外的坦赞铁路

1964年1月18日,在我参加工作的第一年,我光荣地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。在国内建设如火如荼时,援非医疗工作也开始启动,1968年4月底,我与同事刘耀农从北京出发到广州,辗转历经13天到达坦桑尼亚。我们俩一个是神经内科大夫,一个是心血管科大夫,就组成了医院第一批支援坦赞铁路的医疗队。
到坦桑尼亚后,因在坦桑尼亚的水利专家组张敏才被蜂蛰伤死亡。为加强医疗,刘耀农大夫跟水利专家组随钻探车医疗保障,我与铁道部勘测三院张清河大夫在伊法卡拉第一队负责医疗保障。

当时条件十分艰苦,帐篷是单层的,支两张行军床,既是宿舍又是诊疗室。医疗设备简陋,没有消毒设施,消毒就用饭盒在锅里蒸。室内温度在40℃左右,太阳下温度达60℃左右。蚊虫很多,有时早晨起来发现蛇爬到鞋口里,白天为防蚊子,都要穿长袖衣服和大头鞋。大部分时间吃的是罐头,没有新鲜蔬菜。大象、犀牛、狮子等随处可见,为防止伤人,每个队都配有8—10支枪。队与队之间比较远,开一天车才能到,野外工作住不上帐篷,枕着原木盖个毛毯睡觉是经常的事。
刚到非洲,由于当地人不了解我们,传了很多谣言,说中国汽车是绿色的,他们抽了我们的血就走了,等等。当地缺医少药相当严重,每天早晨起来,帐篷外跪了一地前来看病的人,黑压压一大片。有内科病,也有外伤,常见的有便秘、疟疾、感染、咳嗽等老年病。由于缺药,我们对烂疮用新洁尔灭加水浸泡纱布覆盖给消炎治疗,三四天换一次纱布,不到一个月就好了,这在当地影响很大,他们说中国大夫有神药。当地人便秘的多,这与他们不吃蔬菜有关,患腋臭的很多,若腋臭喷上香水非常难闻,看一上午病,被熏得中午都吃不下饭。我当时感染了疟疾,因为人手紧张,发高烧时还要给患者打点滴。

在非洲的医疗过程,有很多传奇的故事发生。当地有一个聋哑病人,经针灸几次后能说话了,病人给我们送来公鸡致谢,这在当地是最高礼遇。
当地野牛多,在一次勘测中,一名叫李锦文的勘测工人被野牛顶断大隐静脉,由于是山地,队长背着他走了五六里地到我们帐篷。由于出血太多,两人成了血人,经检查脉搏摸不着、精神淡漠、测不到血压。血管都瘪了,点滴扎不进去。静脉切开打了5000毫升生理盐水和葡萄糖,才测到血压。清理伤口中血块、草叶等杂物一大碗。我虽是神经内科大夫,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也必须做手术。我和张大夫从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多才完成手术,结扎了静脉。病人血压上来了,后经治疗,40天后痊愈。以上两件事在当地造成了轰动性影响,都赞扬中国大夫是神医。自此以后,病人就越来越多。
除正常医疗外,我们还要随访调查,到麻风病村与麻风病人交流。当地性病、黄疸病也不少,还有埃及吸血虫病。为了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,冒着被传染的危险,我们每天都要处理形形色色的当地病人。

作为共产党人,就是一块砖,哪里需要哪里搬,我一共去坦赞铁路行医4次,前三次是在坦桑尼亚。第四次在赞比亚的时候,各方面的条件就比前几次好多了。每次出国都是两年,前前后后共10年的时间,我把青春挥洒在共和国的友谊路上,这段时间成为我人生最难忘的经历。作为一名大夫,必须博才多学,更要深入实践,将自己的价值用在祖国和党最需要的地方,援非虽然艰苦却让我的人生充实。这就是四次援非医疗经历给我最大的启示。
如今,81岁的我每每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,庆幸自己迎来了建党100周年,欣喜地看到我们的祖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如此繁荣昌盛,我的眼里总是被抑制不住的泪水充盈,在心里默默祝福:中国共产党万岁!祖国万岁!